女鼓手约翰・勒卡雷小说pdf免费版|百度网盘下载
编者评:英国首屈一指的间谍小说大师史诗
在巴以冲突背景下上演的《色戒》,韩国著名导演朴赞郁首次执导谍战剧,英剧《鼓手》热播BBC,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大师的史诗巨作。最新版女鼓手pdf为大家免费附上,需要自己去拿。

女鼓手小说pdf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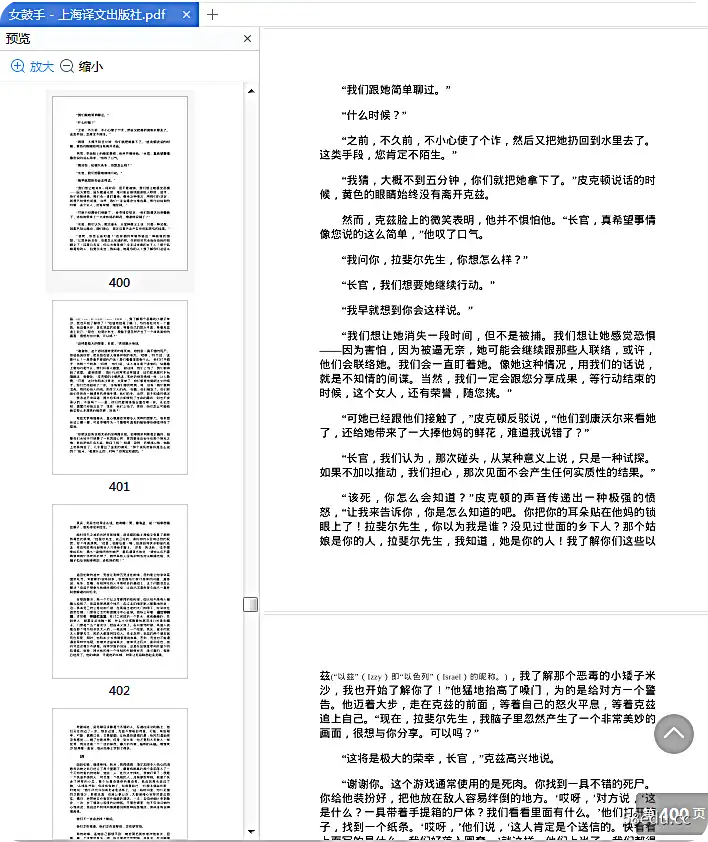

简介
《鼓手》是一部在巴以冲突背景下上演的《色戒》:以色列间谍首领马丁·库兹暗杀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利勒,他是欧洲长期的犹太人目标,实施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头目出击——招募了激进的左翼英国女演员查理。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查理终于融入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面对虚构的恋人和经历,查理的良心和道德不断在两国之间折腾,根深蒂固的道德价值观被撕成碎片。哪一边是对的?作为一个向往爱情的脆弱双女间谍,你应该如何选择?
精彩的书摘
我从没想过这次行动的后果,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震惊了世界。很确定查理是唯一一个留在黑暗中的人。每个人都知道——只要研究一下盎格鲁-撒克逊报纸国际新闻版的副标题——一名疑似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西德精锐武装部队杀害,并劫持了一名姓名不详的妇女作为人质。 ,被紧急送往医院,虽然处于休克状态,但没有生命的恐惧。德国报纸也故意夸大了这一点——“一部疯狂的西部片在黑森林上演”——各种版本,不一样,但大多数都对报道的内容发誓。这样一来,它就失去了价值。弗莱堡针对明克尔教授的爆炸未遂,先是被报死,后来又说死了,被温文尔雅的亚历克西斯博士巧妙地否认了,所以,大家只能相信了。但是,借用那些聪明的政客枪手的话,隐瞒一些事情是完全正确的。
西半球的一连串小案子引起了人们对几个阿拉伯恐怖组织活动的关注,但随着近来反对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很难分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例如,最近,瑞士人文主义律师、少数族裔权利捍卫者、著名金融家之子安东·梅斯特宾博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西班牙极端组织长枪党暗杀。该组织最近公开挑战欧洲人,谴责他们对巴勒斯坦“占领”黎巴嫩的同情。枪击发生在受害者走出家门准备上班时——像往常一样毫无准备。至少那天早上,全世界都震惊了。慕尼黑一家报纸的编辑收到一封署名“解放黎巴嫩”的信,声称对谋杀负责,并说这是真的。为此,一位年轻的黎巴嫩外交官被要求离开德国,他明智地离开了。
一名拒绝阵线外交官在圣约翰伍德一座新建的清真寺外的汽车中被炸弹炸死,这是几个月来发生的第四起此类案件,但很少引起关注。
另一方面,意大利音乐家和报纸专栏作家阿尔伯特·罗西诺 (Albert Rossino) 和他的德国女同伴被残忍地刺死,几周后在蒂罗尔湖 (Lake Tyrol) 附近发现他们的尸体赤裸着,血腥且难以辨认。奥地利官员表示,虽然遇难者都与激进组织有关,但此案与政治无关。根据他们掌握的线索,他们将其定性为激情犯罪。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阿斯特丽德·伯格,据说她喜欢与众不同。虽然很难理解,但很可能没有第三方参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其他谋杀案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包括以色列轰炸叙利亚边境的一座古老堡垒,耶路撒冷的情报部门称该堡垒是巴勒斯坦训练外国恐怖分子的基地。在贝鲁特郊外的一座山顶上,一枚重达 400 磅的炸弹爆炸,摧毁了一个豪华的避暑胜地,并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包括 Tayyeh 和 Fatme。就像那个贫困地区的其他恐怖一样,这个同样令人费解。
然而,住在海边院子里的查理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只知道粗糙,出于无聊和恐惧,她拒绝细节。起初,她只是在沙滩上游泳、散步、来回走动。保镖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直跟着她,但她还是习惯了抓着睡衣的领子护住喉咙。在海边,她喜欢坐在没有风浪的浅滩上,用海水洗脸、洗胳膊和洗手。其他女孩按照要求赤身裸体地在海里游泳,但查理拒绝像她们那样自由地游泳。心理医生对姑娘们说,穿上衣服等着吧。
Kertz 每周来看她一次,有时两次。虽然她经常生他的气,但他很温柔,很有耐心,对她很忠诚。他带来的消息很实用,而且大部分都是对她有利的。
他说他给她安排了一个教父,一个她父亲的老朋友。那个之前发了财的男人,最近在瑞士去世,留给她一笔财富。因为这笔钱来自国外,所以在英国免征资本转移税。
他说已经通知了英国官员,并且得到了对方的批准——原因不需要让查理知道——不会对查理与欧洲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查团体。 Kerz 还表示,Querrey 对她的评价很高。警方特意拜访了奎里,向他解释他们之前对查理的怀疑是误会。
此外,Kerz 就她突然离开伦敦的原因征求了查理的意见。查理被动地接受了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她对警察骚扰的恐惧、轻度抑郁,以及在米科诺斯之后,她遇到了一个神秘的情人,一个已婚妇女。丈夫,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最后抛弃了她。然而,当他刚刚开始给她灌输这些,测试她对其他细节的记忆时,她脸色苍白,身体在颤抖。当克兹郑重地告诉她——时机不对——最高领导层已经裁定她可以在未来任何时候成为以色列公民时,她也有同样的反应。
“为了法特梅,”她厉声说。克兹接手了很多新案子,一时想不起来法特玛是谁,只好又查了一遍档案。
对于她的演艺事业,Kerz 表示,一旦她准备好了,就会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在等着她。在她缺席期间,几位好莱坞制片人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渴望看到她去西海岸试镜。其中一个人手头有一个现成的小角色,可能很适合她。具体的事情,Kerz 也不是很清楚。此外,伦敦舞台上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查理说。
Kertz 说,没问题,他会安排的,亲爱的。
精神科医生是个优秀的年轻人,身材高大,眼神犀利。他有服兵役的背景,并不特别关注自我分析或其他形式的内省。坦率地说,他的目的似乎不是让她说话;相反,他希望她相信她不应该相信。他在他的行业中一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带她兜风,起初只是在海边的路上跑,然后就直奔特拉维夫。路上,他也没多想,指了指路边尚存的几座漂亮的阿拉伯建筑给她看。没想到,她因为愤怒而失去了对情绪的控制。他带她去偏僻的餐馆,和她一起游泳,甚至和她并肩躺在阳光下。他极力想和她搭讪,后来,她用一种很怪异的语气告诉他,如果她有话要说,她宁愿去他的办公室说。听说她喜欢骑马,立马就订了马,玩的真好,她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第二天,令他惊讶的是,她又陷入了沉默。至少再过一周,他告诉 Kerz。那天晚上,奇怪的是,她突然开始呕吐了很久。她之前吃的不多,这种现象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罗谢尔来了。她回到学校继续她的学业。与查理在雅典第一次见到她时不同,她坦率、亲切、非常轻松。迪米特里也回学校了,她说,拉乌尔正在考虑上医学院,打算将来成为一名军医;如果没有,请学习考古。听到家人的最新消息,查理礼貌地笑了笑。之后,罗谢尔告诉科茨,她有一种坐在祖母对面的感觉。最终,她在英格兰北部的成长经历和中产阶级悠闲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记。过了一会儿,查理更有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在库尔兹的部门,技术和人文知识是支撑无数行动成功的宝库。现在,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已经添加到这个宝库中。尽管对非犹太人的偏见根深蒂固,但必须承认,他们不仅有用,而且有时不可或缺。没有哪个犹太女孩能如此坚定地站在中间。技术人员对闹钟收音机中的电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活和学习。一个被删除的案例被及时挖掘出来,用于培训课程,效果非常好。有人说,理论上,情报人员在交换物品时应该注意到间谍的闹钟没有电池。不管怎样,当返回信号被中断时,他至少从情况推断,果断地冲进了屋子。当然,贝克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这些材料上。这和安全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克雷兹最近没听到有人说贝克的好话,所以他不想封他。
一转眼,已是晚春,利塔尼盆地已完全干涸。 Quetz 最大的恐惧和 Gavron 的最大威胁即将消失,期待已久的以色列坦克进入黎巴嫩结束了当前的敌对行动阶段;或者,换句话说,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曾经收容查理的营地被清扫了,换句话说,在坦克和高射炮之后,推土机进来埋葬尸体并抹去痕迹。幸存的难民开始向北迁移,留下成千上万的尸体堆积在他们身后。在贝鲁特,特种作战小队摧毁了查理曾待过的秘密据点;在西顿的房子里,只剩下那只小鸡和一束黄褐色的兰花。房子被侦察队摧毁,两个名叫卡里姆和亚西尔的小伙子被杀。侦察小队趁夜色从海上潜入,与大情报官亚瑟尔的预测完全吻合,使用的是美制爆炸弹头。这是一种秘密武器,如果它接触到受害者的身体,就会当场杀死受害者。这一切——她与巴勒斯坦短暂的恋情被抹去——查理无从知晓。心理医生说,如果她被告知,她的世界就会天翻地覆,因为她的想象力和自我放纵,她很容易登上顶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好让她蒙在鼓里,等她痊愈后自己去发现。至于基兹,一个多月来很少见他;即使他这样做了,他也可能不会被认出来。他的身体仿佛一下子就缩成了两半,斯拉夫式的眼眸中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一句话,他老了很多。有一天,他像一个大病痊愈的人一样回来了。几个小时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容貌,准备与加弗伦开战。
作者介绍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约翰·摩尔·康纳,英国间谍小说家。早年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后开始以笔名写小说。勒卡雷以长篇小说《柏林间谍》一举成名,被当时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称赞为:“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从此,他确立了文学大师的地位。
勒卡雷一生赢得了无数奖项,包括 1964 年的英国毛姆奖、1965 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埃德加爱伦坡奖和 1988 年的英国推理作家协会 (CWA) 终身成就奖。 1963年和1977年获得金匕首奖)等。 2008 年,勒卡雷在《时代》杂志的“1945 年以来最伟大的 50 位英国作家”名单中排名第 22 位。 2011 年,Le Carré 被歌德学院授予歌德奖。
勒卡雷的作品不仅吸引了全球各大媒体和读者的关注,还因其戏剧元素和张力而多次被翻拍成影视剧。 2018年11月,《鼓手》由韩国著名导演朴赞郁执导,翻拍为6集迷你剧,在BBC播出。
在线免费试用
冷战结束时,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笑得开心,迫不及待地断言,从现在起我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他们说:勒卡雷的工作彻底毁了。
事实上,在我迄今为止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名作家,我比其他人更快乐,因为柏林墙终于倒塌了,我可以专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方面。那些研究苏联政治制度的学者,那些谈军事的文人,还有那些国防记者,此刻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领域。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很久以前就画好了我的地盘。创作于 1981 年至 1982 年间的《鼓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时候,冷战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个故事里没有乔治·斯迈利,这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故事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主人公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是关于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长期战争。停止!停止!对不起,我已经表明了我的偏见。那些年,在以色列,我不断地向我灌输巴勒斯坦不是一个国家;巴勒斯坦人是一群农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两千年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照看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回来!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很艰难。当我开始写作时,我的脑海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布局——我通常的风格——我无法预测哪一方会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为战后在奥地利的一名年轻情报人员,我审讯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困境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反犹太主义,我理解,但上帝作证,与我在欧洲大陆和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相比,它相形见绌。
可以这么说,我对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了几年。那时,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在我看来,总是很自大。即使他们研究其他领域的问题,他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让别人望而却步。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分子虽然规模小得多,但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或许,虚拟的外交舞台与约瑟夫的真实剧场是一样的。谁能分清是非!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事处。当时,相邻的屋顶上都有摄像头,几个无聊的魁梧男子在街上漫步。我不知道那里现在发生了什么,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去过那里。再也没有去过中东,再也没有去过绿街。一旦工作完成,那些地方就没有了。
当时住在绿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见他。在那之前,我给了他一本时代杂志,封面是我迷人的脸。在电话中,我提到了我们一起认识的几个人。 “是的,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棕色男人的声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能谈谈,我会请他吃午饭。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给我的一切:推荐、建议、提醒、激动,甚至是谎言。不管内容是什么,我都不介意。我想听听这两个故事。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来说是新的,我决定优先考虑他们。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情报官员乔治·斯迈利是勒卡雷多小说的中心人物。
我按了门铃,街上无聊的魁梧男子茫然地看着1、同样,屋顶上的摄像机也对准了1、门打开,我进入一个玻璃亭,形状像竖立的水晶棺材,外面有守卫。在他身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穿着西装笔直地站在那里,透过玻璃看着前面的门厅:一座美丽的 18 世纪建筑。两个大阿拉伯男人,阴沉着脸,恶狠狠地盯着1、玻璃门打开,我走进门厅。那两个人来找我搜查我:漫长、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专业方法。在特拉维夫的卢尔德机场,在通往亚西尔阿拉法特临时总部的接待室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在格林街,这个项目仍然存在,或者已经存在。无论是阿拉伯保镖,还是犹太保镖,他们不只是在搜查你,他们在用手和眼睛盘问你,他们在捕捉你的身体对他们手的可疑反应。关键是时间。他们喜欢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只是想让嫌疑人知道他自己的私处,他的口臭,他自己的恶意。我什至不记得在创作《女鼓手》的过程中被搜索了多少次。然而,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相遇往往都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发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街,当时我正在拜访拉姆拉维先生。
当然,拉姆拉维先生从未出现过。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他的日记里没有约会之类的东西。他的秘书也从未听说过1、他在国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来。再过一天,将是另一个第一次。从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阿拉伯人接待了我,他们总是把我放在一边。就在会客室发生的事情,恐怕我可以写一本书了。不过,拉姆拉维先生的缺席给我带来了炮火的洗礼,这有点恶趣味,因为他在伦敦的前任被枪杀,不久之后拉姆拉维本人也在西班牙被杀。 ,或者被炸弹炸死,具体记不清了。不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会死。
在去格林街之后,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首先,我联系了著名的阿拉伯文化专家和作家 Patrick Searle。我邀请他吃午饭,这应该是和 Ram Ravi 一起吃的。自塞尔以来,我的社交圈逐渐扩大。事情就是这样,你正在经历内在和外在的发展:从朋友到朋友的朋友,我被推销并接受各种意见。我的电话一直在响,每个人都想给你建议,以及如何避免犯某种致命的错误:我的生活最终变得非常忙,试图了解巴勒斯坦人。
结果,也是最重要的,我认识了侯赛因国王的第一任妻子约旦公主迪娜。此时,她嫁给了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亚西尔·阿拉法特青年卫队的领导人萨拉·塔马利。在伦敦,迪娜悄悄地来来去去。萨拉更像是一条龙。不管是什么活动,从来都不是很准时。应该说这是故意的。不过,最终,我们三个人在西区的一家高档餐厅聚在一起。在这次延迟开始的午餐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莎拉关于太平洋鲽鱼和巴黎矿泉水的激烈演讲。他热情洋溢,口音纯正,言辞优雅,表情生动,让旁边一桌的客人都傻眼了。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莎拉邀请我住在他们西顿的家中。萨拉还答应把贝鲁特的朋友介绍给1、作为对他们慷慨的回报,我尽可能地透明和坦诚,我打出了明确的牌:我也会去以色列——虽然我很快就学会了叫它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窥探任何秘密,我只是希望能够坐在他们的辩论中,亲眼看到双方的辩论者。然而,人们仍然称我为英国外交部的喉舌。是的,我确实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所以这种善意的猜测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无法摆脱。也许,这对我有利,因为,直到今天,我不知道,一些最终同意见我的人,如果他们相信真相——我只是一个寻找素材的小说家——他们还会如此慷慨吗? ?外交部,如果它记得我,它一定恨1、
从那时起,我就像查理一样,一直在情绪的钟摆上,前一刻,这样,下一刻,那样。我通常途经塞浦路斯,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侨民之间旅行。本周,我将与巴勒斯坦人一起前往黎巴嫩、约旦或突尼斯;下周,我要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或者内盖夫,或者,(不幸遭遇痢疾)从约旦一侧,穿过艾伦比桥。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卫格林威,他当时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我将永远记得痛苦地躺在后座上,看着大卫自信地大步走过一排等待检查的卡车,直奔检查站,随便喊出他认识的每一位东方要人的名字。不,说服警卫让我们先通过。还有一次,我和格林威包车前往黎巴嫩南部边境的一座古老的十字军城堡。那时,巴勒斯坦人仍在被占领土上——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永远无法分辨,更让我害怕的是:山谷中狙击手的子弹?还是我们德鲁兹司机的驾驶技术?每次急转弯,都难免被人折腾在车里,那家伙就是会哼两声祈祷。那时,格林威恰好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样,对双方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早些时候,我在写《荣誉学生》时,他恰好在东南亚,先后受雇于时代杂志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战争。
我太幸运了!在创作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能够跟随他。他有记者的勇气,有记者的智慧,这些都是我无法企及的。
在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之前,我等了很久。在贝鲁特,在通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公室的那个该死的小接待室里,我感到愤怒的是,我浪费了无数个小时,别无选择,只能等待。在当天的演讲者——一位名叫拉帕蒂的绅士——出来迎接我之前,我仔细观察了房间里展示的以色列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上面全是灰尘。我几乎要窒息了,因为阿拉法特的许多英雄都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室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雾。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张巴勒斯坦人的脸。所有的战士似乎都有这张脸,即使是胖子:一张绷紧的、囚犯灰色的脸,一副飘忽不定的神情,整天和垃圾食品、香烟、神经紧张的伴侣在一起。哇,革命有钱。看看他们全新的制服和靴子,全新的车辆,全新的电话,全新的武器。被剥夺的感觉来自金钱以外的东西,爱、希望、朋友和家人的缺席。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来说,再多的金表也无法弥补他们所遭受的伤害。甚至没有莎拉·塔马利。无论他出现在哪个房间,他那传奇般的潇洒——再加上他的口才和人道主义——都令人着迷。尽管如此,他还是逃不过巴勒斯坦人的脸,他也不想。当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他们终于俘虏了他——他们俘虏的最高级别的巴勒斯坦人。正是因为莎拉意识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经过几个月的单独监禁和审讯,他战胜了自己,并以温和和共同立场的声音出现在以色列电视屏幕上。
我会在您下榻的酒店与您联系。有人叫我在酒店等,记住,等。
正在等待写入。我蹲在贝鲁特的 Commodore Hotel,在里面的酒吧里花了不少钱,那里的鹦鹉已经可以模仿贝鲁特进出的声音了。夜里,我听到外面持续不断的枪声,从卧室漆黑的窗外望去,山后的火焰在闪烁。我在一家空荡荡的中餐厅吃了炸春卷,酒店的工作人员很棒,不知道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还能照常营业需要什么条件。吃饭的时候,我竖起耳朵,密切注意前台发生的事情。
最后,一瘸一拐的服务员给我带来了通知。感觉他的腿大概是少了大部分,但因为他年轻有活力,所以外人很难看出他的腿伤是什么。我刚要把结实的春卷塞进我嘴里,他踉踉跄跄地走过空荡荡的桌子朝我走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们的董事长现在要见你,”他低声对我说,严肃而严肃,仿佛我们在搞什么阴谋,“现在,快点!”
但是,我真的很愚蠢。很明显他想让我站起来,所以,出于礼貌,我站了起来,以为他想带我去他们酒店的董事长。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住得太久了,还没有付账?或者,主席要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签名簿上?或者,是真的,还是想象的,我毁了酒店的财产,他想把我踢出去?在贝鲁特,每个人的行为,包括我自己,都是不可预测的。
我跟着男孩穿过酒店大堂到前门。我看到一小队士兵穿着斗篷一样的外套,双手藏在衣服的褶皱里,门外还有两辆卡其色的沃尔沃,我恍然大悟,他们正在带我去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 .
《鼓手》一书中的某处,有类似的描述:夜晚,贝鲁特,穿越城市,换车,隐身,时速九十英里,撞穿中间的分隔线——车道,大灯闪烁,向相反方向行驶。这是那天晚上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一座经历过炮火和维修的高层建筑,大约有十一层或十二层高。最后,士兵来搜查1、这种待遇我经历过无数次。我失去了耐心,无耻地说我受够了。他们微笑着向我道歉,然后退到一边,护送我到阿拉法特身边。他戴着一把银色手枪,穿着熨烫得很好的军装,散发着婴儿爽身粉的味道。我们礼貌地拥抱了一下,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胡茬是银色的,不是太刺眼。
“大卫先生,你怎么在这里?”他问。没想到,他直呼我的名字,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看着我的眼睛,就像一个担心的医生。
“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脏上。”
他抓住我的手,按在他的胸口。他的手软软的,像女孩的手。
“大卫先生,在这里,就在这里!”
无一例外,阿拉法特也有那张巴勒斯坦面孔。他的脸可以像灯塔,熠熠生辉,也可以像小丑,表情夸张,也可以更像政客,庄重严肃。他的眼睛是如此明亮,以至于你会忍不住对它们做出反应,除非你是个吝啬鬼。 When he speaks, from time to time, he will be in high spirits, breaking the routine with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He can guide you like a teacher, and when he listens to your statement of wisdom, he acts like an obsessed student. However, between the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roles, you see another face, the face of an overly sensitive little warrior. He lost his warhorse, and you have an irrepressible urge to help him find that horse.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Arafat, which was what I had hoped for. I want to be conquered like the Charlie I made. I want her to be a woman with a double promise and for both parties, and therefore, destined to betray them too. In this way, in the fashionable phrase of the moment, I follow the trend: Follow two trends, two diametrically opposed trends. When I was in Seton, I lived at Sarah and Dina's, a beautiful house scarred by war, with goats in the yard, lemon trees, cats and dogs.我聆听萨拉热情却又不失同情心的雄辩,还听到了担任我警卫的那几个小战士的故事,经历了――此刻,写作过程中,再一次经历了――悲悯夹杂着勇士的斗志,查莉的控制人,约瑟夫,最擅长的就是开发、利用这种复杂的情感。
***
那么,怎么解释恐怖活动呢?你愤愤地问。暴力活动呢?还有,犹太校车上的炸弹?难不成我真的是过分乐观、愚蠢低能,竟然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吗?
哇哦,我什么都明白。
哪怕你在贝鲁特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你也能嗅到门外的恐怖气息。哪怕你是个门外汉,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你也能分辨出,跟你说笑的那些人,一半以上都应该平躺在心理治疗师的治疗床上。此外,你还能意识到,自从婴孩时起,他们的生活就完全错位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暴力,他们已经学会将“正常”的社会视为敌对的靶子。那些被视为贱民的人变成了贱民――引用奥登的话来说,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将邪恶报以他人。
我跟一个极端组织的代言人交谈过,这伙人公开脱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团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装,懒洋洋地靠在墙根下。东道主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带相框的高清图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喷气式飞机,地点是一个报废的机场。炸弹爆响的时候,机身的中央完全爆裂开来。那一次,他们在炸毁飞机之前,先行撤离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年轻人个个情绪高涨,一个漂亮的女孩儿给大伙儿端来了阿拉伯咖啡。帅气的勇士们皱着眉,自顾自地喝起来。有个家伙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划着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那么,杀戮呢?我问。东道主被我问懵了。他吸了一口气,用官方的口吻说: 一枚以色列炸弹,落在南黎巴嫩的一个聚集点,造成了无数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死难的人数超过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灭的犹太人数的总和……这不是杀戮,这是战争……这是自卫……我走出房间,来到户外。如果不是战争,此地的空气应该和贝鲁特大街上的一样清新。
说说以色列吧!为什么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经历呢?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以色列人易于接近,他们有门铃,有正常的工作电话,还有漂亮的房屋、学校和护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谈,无须犹豫,十有八九,你的心愿可以达成。官方的说辞,听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没有人故意刁难1、将军们通常只穿着衬衣,看见我来了,他们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并给我足够的时间提问。政治家、情报官,以及报社编辑,他们在一起交谈、辩论,气氛和谐,而这一切,从哲学的角度说,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见不到的。
胜利并没有让以色列名声大振,但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从本能讲,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众,众所周知,他们自发地四处移居,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世界大游戏中的一个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美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公共关系的较量中,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大卫,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了哥利亚。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恐怖组织把巴勒斯坦大旗钉在他们的桅杆上。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两边摇摆。
三年后,这本书被采用了。跟我的写作经历一样,这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么改变。以色列人比较随和,给与了好评。在美国,之前的任何畅销书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因此说,我的书,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卑劣地指责我,说,批评以色列,理论上说,就是反犹太人。对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来自美国的犹太组织,对我进行谩骂和诋毁;也有一些来自个人,那些犹太人的信件,内容非常感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耐心地看完了我的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认为这本书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写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体对此书反应平淡,褒贬不一。一位重磅级的阿拉伯批评家认为此书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说和现实一样,巴勒斯坦都是输家。
至于我本人,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时,我一反常态,感觉非常坦然。我发现,我主要的遗憾在于,开始部分,对德国人的描述有些过长了;我最大的难过在于,无须做任何改动,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约翰・勒卡雷1993年4月作家感言
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心怀窃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断言,认为从此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素材了。他们说: 勒卡雷的饭碗彻底砸了。
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个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觉更加幸福,因为,柏林墙终于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我们时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苏联政体的学者,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那些防务记者,此刻,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疆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了我的地盘。创作于1981年到1982年间的《女鼓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冷战还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乔治・史迈利①,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的主角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战争。停!停!抱歉,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偏见。在那些年月里,在以色列,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以下的观点: 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两千年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归来!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贯的风格――也预测不出究竟哪一方会赢,唯一确定的是,作为一个战后活动在奥地利的年轻情报官来说,我曾经审问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苦难境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层中的反犹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证,相比较我在欧洲大陆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到的,那可就大为逊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可以说,我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们,在我看来,总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气。哪怕他们研究的是其他领域的问题,他们依旧自成一体,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色列分子,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举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许,虚拟的外交舞台和约瑟夫真实的戏院一样,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公室。那个时候,毗邻的屋顶上架着摄像头,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在街上溜达。我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再也没有去过中东,也没有去过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跟他见面。在这之前,我给他送了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头像。电话里,我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人。 “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褐色皮肤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谈得来,我就邀请他共进午餐。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够提供给我的一切: 引荐他人、建议、提醒、鼓动,甚至谎言。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不介意。两边的故事,我都想听。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决定把优先权给他们。乔治・史迈利,情报官员,供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MI6,是勒卡雷多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
我按响了门铃,街上那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1、同样,屋顶的摄像机也对准了1、门开了,我走进一个玻璃亭子,形状像竖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卫。身后,门咔地一声关上了。我西装笔挺地站在那里,目光穿过玻璃,打量着前方的门厅: 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两个阿拉伯大汉,面露愠色,狠狠地盯着1、玻璃门开了,我迈步进入门厅。那两个人来到我身边,对我进行了搜身检查: 长时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职业手法。在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在通往亚西尔・阿拉法特临时司令部的接待室里,也经历过如此的遭遇。现在,在格林大街,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无论是阿拉伯保镖,还是犹太保镖,他们不只是对你进行搜身,他们用手和眼睛盘问你,他们在捕捉你的身体对他们的双手作出的可疑反应。关键是时间。他们爱折腾多久,就多久。他们就是想让嫌疑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图。创作《女鼓手》期间,我究竟被搜过多少次身,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的遭遇,往往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就发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访拉姆拉维先生之际。
自然,拉姆拉维先生始终没有现身。我一个人呆立在门厅里。在他的记事簿上,根本没有约会这码事儿。他的秘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1、他在国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来吧。改天,那将会是另一个第一次。打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个阿拉伯人接待过我,他们总是打发我等在一边。单就发生在接待室里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维先生带给我的是炮火的洗礼,这个玩笑有些不厚道,因为,他在伦敦的前任被枪杀了,而且,拉姆拉维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弹炸死的,具体我记不清了。尽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不会消亡的。
......
约翰・勒卡雷1993年4月作家感言


